正如金庸筆下的江湖人物,個個都身懷絕技而又風格迥異,在中國的地產江湖中,房企大腕們便是現代版的江湖人物,遠見者如王石,思考者如馮侖,投機者如潘石屹——他們的共同點似乎是都習慣于生活在聚光燈下。而低調者如凌克,則寧愿選擇在臺燈下工作。
作為金地集團的掌門人,53歲的凌克是個十足的完美主義者,他不僅在戰略層面把握方向,也從未放松對細節的關注。
完美主義的他事事較真,不管在工作中抑或生活中,他都習慣用自己的高標準嚴加要求自己和身邊的人。而這似乎又是一把雙刃劍,追求質感的金地集團似乎面臨著效率低下的困惑。
理想主義的他喜歡思考,在地產行業如火如荼的年月,他已開始反思這個成長快速、賺錢也快速的行業,將會面臨怎樣的膨脹邊際,又將怎樣通過產業領域拓展和發展模式轉型,實現更長遠成長。
他具有很強的雙面性。在員工眼中,他外表嚴肅,不茍言笑得甚至有些令人生畏。而在他的內心,卻是地道的俠義柔腸,他關心員工的健康,并在百忙之中照顧弱勢青少年。
從深圳福田區下轄的一家地方企業成長為全國性開發商,金地只用了十余年。無疑地,這種成長速度在全國范圍內都屬領先;而另一方面,曾名震股海的“招保萬金”如今已明顯劃分為不同的梯隊,金地明顯落后于萬科,甚至諸如恒大、碧桂園等后起之秀。
在慘淡的行情中,凌克對2011年的業績顯得還比較滿意,但也提出,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將要學習“冬泳”。
成功屬于時代的產物
如果不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浪潮,凌克或許在湖北的一家軍工企業當上了廠長或總工程師。他的身上有著很強的時代烙印。
1978年,凌克參加了第一屆高考,大學畢業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名工程師,分配至一家軍工企業;1988年,受到十三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他選擇下海,涉足房地產,開始人生的轉變。
談及當年的抉擇,他稱并無后悔,“改革開放的思想、振興中國的思想召喚了我,使我可以放棄原來這些工作,投入到一個自己非常陌生的工作當中”。
自小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他并不避諱這一點,這種舍己為人的精神在他的腦子里根深蒂固,而他堅信,如果將來有什么可以再次讓他熱血沸騰,那一定是振興中國,帶領企業走出國門。
當年受到改革開放召喚的凌克剛到深圳時并不是一帆風順,他做過報關員,直到他加入金地集團并以坐直升飛機的速度晉升為董事長,才算進入事業的正軌。
那是在1998年,中國住宅商品化改革啟動,凌克在這一年接任金地董事長。從普通員工到董事長,他僅用了短短六年的時間。
2001年的上市成為金地的新起點,讓其成為繼萬科和招商地產之后的股市新秀,并逐步實現100倍的規模增長。
從某種程度上說,凌克的成功基于中國房地產發展的黃金十年,而在他亦承認,“我的成功肯定是時代的產物,不僅是我,這一代企業家的成功都應歸功于改革開放的政策。”
而今,在嚴苛的宏觀調控政策下,昔日輝煌的開發商不得不反思行業的前景問題。凌克承認,房地產高利潤的時代已經結束,但持續發展的動力依然存在。
他喜歡用數字來說話,“中國有3.7億個家庭,但是我們中國成套住宅還只有2.7億套,所以我們中國還需要1億套住宅,而目前的情況是每年可以生產1000萬套住宅”。
盡管前景依然美好,但變數卻增加不少,在這種背景下,很多開發商開始尋求轉型之路,“快速開發、現金為王”成為主旋律。
2010年以來,凌克領導下的金地集團則將“金融”和“商業地產”作為集團兩翼,高調進軍商業地產,搶灘金融市場。而在我們的訪談中,凌克首次提到了效率之說。
效率低下之惑
一位地產人士如此評論凌克:他是一位很有想法的管理者,但由于某些原因,想法很難在公司內積極地推進。
這里所謂的“某些原因”似乎含義深刻。金地起源于廣東深圳,2003年開始進軍全國,最初戰果頗豐。2003-2004年,金地曾一度與第一梯隊的開發商如萬科、中海發展等相差無幾,直到2008年,中國開始上一輪樓市調控時,金地開始掉隊了。
數據顯示,2008年,金地銷售額僅過百億元,同年萬科銷售額卻接近500億元,距離逐步拉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金地在高速發展的浪潮之后開始落后于第一梯隊?在與我們的對話中,盡管凌克認為將金地與萬科置于同一個賽道并不合適,“我們比萬科晚上市10年,這樣單獨來比較恐怕不太合適”。
但同時,凌克又表現出坦蕩的一面,他反復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并承認金地集團目前的效率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金地的節奏確實比同行要慢。在產品生產上,金地就要花比別人長得多的時間。”這似乎再次印證了凌克完美主義的作風:精益求精、追求高品質。在他的經營哲學里,“好不好”比“快不快”是更為重要的命題。
不過,凌克卻也開始反思效率低下的問題。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若有所思道:“過去這幾年我們還不夠快,所以我們最近正在努力地改變,比如說我們現在在產品的設計方面要求更快,我們建立了自己的標準化產品線,使產品設計周期在變短,同時質量、品質都還得以保障。”
前有標兵、后有追兵,金地的位置有些尷尬,一面要追趕跑在前面的萬科、保利等,一面又要隨時提防被后起的一批新秀超越。
面對內外交迫,金地的轉型似乎已經迫在眉睫。不愿犧牲產品品質的凌克選擇了另一條路徑:既快又好。
理性與野心
與“文科萬科”相較之下,人們給金地貼上了“理科”的標簽。理工科出身的凌克謹言慎行,有時候甚至表現得不善言辭,只做不說。
據金地員工說,不僅凌克,金地高層很大一部分都是理科出身。在凌克們的理性思維下,金地集團實現了快速擴張和風險控制。
金地2011年財報顯示,公司凈負債率下降了7.6%,而資產負債率為71%,低于同類企業,可見金地將財務風險控制放在首位。
盡管手握大量現金和預收賬款,但對于2012年是否買地仍然保持謹慎意見。
現金為王,在嚴厲的房地產調控背景下,金地無疑保持住“穩健”的資金流。但也有人質疑,過于保守的金地或許已經錯失快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機會。
凌克笑言,理工科的管理層會多幾分理智,少幾分浪漫,但這并不影響公司的經營,經營主要與戰略相關,這主要取決于是否有一批優秀的人才和企業文化。
盡管腦子里滿是理性,凌克或許并沒有意識到,一向“克制”的他少了一些野心,雖然他自認為并不是一個敢冒險的企業家。多年的商場經驗告訴他,風險控制甚至比擴張更為重要。
從出身來看,金地與萬達這兩家房企有某些相似之處:兩者都帶有國企的血統。金地隸屬于深圳市福田區政府,而萬達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大連西崗住宅開發公司。
1994年,金地向深圳市體改辦提出申請,進行“現代化企業制度改革試點”,并得到批準。而萬達亦在這一時期積極地展開了股份制改革。
不同的是,時至今日,金地的最大股東依然有著政府背景的福田投資發展公司,據最新的財報披露,凌克僅持有公司股票不到1% ;相比之下,王健林則步步為營地將萬達的股權私有化,他本人實際控制的萬達商業地產的股權比例達到62.127%。
盡管“發跡”的路徑類似,但兩位大佬的風格卻迥異。王健林主張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凌克則踐行著精心打造的理念。
不過,凌克似乎也在開始反思如今的競爭格局,“金地公司挺人性化,但是在競爭性、執行力方面略顯弱了一些,我覺得應該要改進,如果不改進的話,也很難跟其它公司競爭。”
夢想
從區屬二級企業的總經理,到金地集團總經理,再到金地集團的董事長,凌克把自己一生最美的時光,鑄進了金地的歷史。
直到如今,凌克還保持著“5+2、白+黑”的工作時間表。盡管他說自己只是指引公司前進的方向的人,但還是要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國內外各大城市。
比起財富,他說自己寧可選擇事業,“因為這會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在約20年時間的“事業”里,對細節精益求精的凌克,既著眼每一棟建筑的打造,又保持了戰略視野的超越。今天的他,甚至又在“夢想”如何將金地帶上國際化的廣闊舞臺。
在地產圈這個江湖中,王石選擇攀登高峰挑戰極限,郁亮酷愛自行車比賽,王健林選擇了“玩”足球,而凌克偏愛網球。他甚至夢想著有一天能當上網球學院的院長。
這個夢想也并非遙不可及。在他的主導下,金地一直以來都在推動網球事業。在他們推出的樓盤中,很多都配套網球場。同時,他們也在推動網球慈善事業。目前,他們還計劃修建一所網球學院。
在此之前,他曾經夢想著退休后能和太太開一家別樣的小旅館,讓青年朋友們可以來入住,每天與他們聊世界、聊人生。
他還特別羨慕王石,能夠“拋下”萬科前往美國哈佛求學。如果將來有機會,他也希望能夠回到校園。
骨子里有一些小小的浪漫,這或許又是理科凌克的另一面吧。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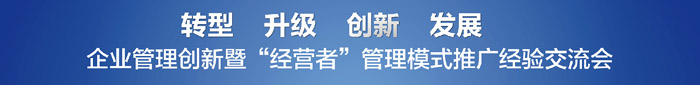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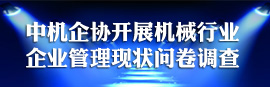

(3).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