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年里,漢能控股通過巨額訂單成為上市公司漢能薄膜發電近乎唯一的客戶,漢能薄膜發電2010年以來的收入,大部分是向母公司漢能控股銷售設備所得。
在關聯交易的扶持下,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和利潤出現快速增長,2012年營業收入27.56億港元,稅后利潤13億港元;2013年營收32.74億港元,稅后盈利20.18億港元;2014年營收猛增至96.15億港元;2014年稅后盈利增至33.07億港元。
收入暴漲的背后是與關聯交易相關的高額應收賬款,從2013年末到2015年末,應收賬款分別達到23億、60億、39億港元。
上市公司并沒有真正面對市場進行銷售,而只是整個漢能這條冗長鏈條中的第一個環節。暴漲的業績伴之以巨額的應收賬款,被批評者質疑為業績造假。
漢能辯解稱,大股東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經過合法披露程序;“體現了大股東對薄膜市場的支持”,“與各國政府對新能源的補貼邏輯相同”。
在銷售暴漲的刺激下,漢能薄膜發電的股價也由2012年底的0.2港元一路飆升至最高點9.07港元,市值最高接近3000億港元。外界驚嘆于李河君身家暴漲,質疑者認為,李河君企圖拉高股價,以便為其超過70%的漢能薄膜發電股票進行高價質押,為漢能開辟新的融資渠道。李河君否認了這個指責,并稱自己不懂資本市場。
遭遇外界的強烈質疑之后,2015年開始,漢能薄膜發電試圖拓展山東新華聯、寶塔投資等新客戶;“5·20”之后,公司連續兩次發布公告,取消與大股東的關聯交易,分別涉及采購金額136.1億元人民幣和5.85億美元。
漢能薄膜發電的年報顯示,2015年,漢能薄膜發電營收28.15億港元,較2014年下跌約70.7%;公司全年虧損122.33億港元。截至2015年底,銀行及其他付息借款為11.83億港元,資產負債比率為31.91%。
在李河君之前,無錫尚德的施正榮、新奧燃氣的王玉鎖、正泰集團的南存輝都曾投資過薄膜行業最后又放棄。李河君說,這個行業需要很多錢,沒有幾百億可能做不起來。“坦率來講,我還是低估了,最后投入比設想要多很多。”
進入薄膜行業之后,漢能一直面臨快速擴張所帶來的資金饑渴。其對外宣稱的九大基地投資2000億,實際遠未達到。生產基地的投入,漢能、地方政府和銀行各出資三分之一,地方政府還低價提供配套土地、補貼等優厚政策支持。
銀行貸款是漢能主要的融資渠道,生產基地建設和生產線融資都比較困難,只有地面電站可以從銀行融資。國開行曾經給予漢能集團300億元授信總額,但實際授出貸款不足1/3。
李河君稱之為“印鈔機”的金安橋水電站是漢能旗下最優質的資產,漢能在云南、廣東等省投資建設水電項目,權益總裝機容量620萬千瓦,相當于2.3個葛洲壩水電站。此前多家媒體報道,金安橋項目和漢能旗下其他水電資產也已經多次抵押進行融資。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獲得的漢能控股2015年半年報顯示,截至去年6月末,公司負債合計553.72億元,期末資產總額761.57億元,負債率約為72.71%。
據悉,漢能停牌前正在準備引入多家戰略投資者,考慮增發新股,融資四五百億元,股價突如其來的暴跌和長時間停牌,嚇退了潛在的投資者和客戶。
內蒙古滿世、寶塔石化、山東新華聯先后終止簽署的股權認購協議,協議認購金額高達275.18億港元,而寶塔投資和北京滿世分別取消了光伏生產線銷售及服務合同,使得漢能薄膜發電減少了154.5億的銷售收入。
“5·20”之后,漢能遭遇銀行抽貸,資金壓力很大,說一年內“還了一百多億”,李河君說:“漢能集團的總體負債情況比較復雜,但最高峰已經過去了,目前負債率是安全的。”至于資金來源,李河君沒有細說,只是說各種渠道都有。
公開信息顯示,漢能薄膜發電以4.3億港元變現了美國的地面電站項目;李河君還以超低價在場外減持了25億股上市公司股票,涉及資金4.5億元人民幣。漢能的光伏基地、地面電站都有變現的傳言,一度還傳出漢能欲將金安橋水電站和上市公司股權捆綁出售變現的消息。由于缺錢,漢能的地面電站項目也幾乎停下來。
去年以來,漢能內部經歷結構調整的“陣痛”:一些部門被裁撤、大量人員被精簡、一些業務被取消;并進行債務重組,新的低息的債務置換了之前的高息債務。
李河君稱,“5·20”暴跌之后,國內有關部門專門組織對漢能進行了調查,調查的結果是“搞清楚了薄膜技術的戰略重要性”和“漢能在薄膜發電領域的地位”。漢能官方網站顯示,漢能擁有的薄膜技術和無人機、太陽能汽車等產品作為科技創新的成果向多位高層匯報。
“企業的危機和困難,本質上是負債危機,沒有負債哪來的危機?”李河君說,經過此次危機,理念發生大的調整,“過去所有環節都是自己做,以后要引入大量的戰投和創投融資”。“過去步子邁得太大,擴張太快。以后要慢慢發展。”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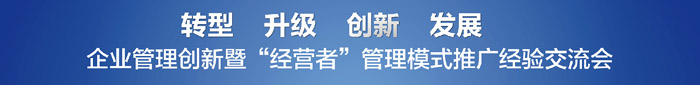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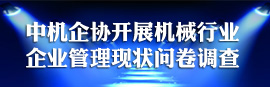

(3).gif)
